五月七日清晨醒来,脑子里闪出“五七指示放光芒”这句话。这么多年了,这段记忆却是越来越清晰,用一篇旧文重温那段记忆,带回我的少年“五七干校”往事。
1970年的夏末秋初,我们这些出生在北京机关大院的孩子们离开大城市,跟随父母去山东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们先是坐上一辆大轿子车,当汽车从天安门前经过时,车上的阿姨们开始哭了。
如今在加拿大当时坐在车上的小伙伴小红在来信中回忆说:“在去火车站的车上,我就坐在赵阿姨身边,过天安门时,她把我举到车窗边一边哭一边说,小红,多看几眼天安门吧,咱们不再回来啦。真有一骨子扎根干校一辈子的决心。”
我们随后踏上了一列开往山东的火车,这列特殊的包车在停停走走两天两夜后,终于到达山东兖州附近一个小火车站。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都在下着雨,乡村的土路满地泥泞。我抱着暖瓶小心翼翼地从泥里拔出双脚,生怕滑倒摔坏了热水瓶。
小红回忆说,从小火车站到八八煤矿那条漫长的泥泞道上,我爸一只手抱着我弟弟,另一只手拉着我。突然从农舍里窜出一条大黄狗,有人吓得开始跑起来,我爸就大声喊着:别跑!别跑!蹲下!蹲下!我的小手被爸爸紧紧地抓着,留下一道道红印。
如今已经退休的新梅感慨地说:我在从程家庄火车站走到八八煤矿的泥泞路上度过了13岁生日,记忆深刻。
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的力红发来回忆给我添不上了我不知道的细节:we had open top truck to pick us up. But the mud was making the wheel spin so it couldn't move. We had to get off the truck and start walking. The roofing was leaking when we go to "baba mei kung".
不知走了多久,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叫“八八煤矿”的地方,那里有十栋有两层楼高的筒子楼,我家在8号楼,分配一南一北两间房,南边住人,北边放杂物。用砖砌的墙面没有涂白灰。
小红在信中问我:还记得我家着火的事吗?那时房子的墙没有涂白灰,我妈妈爱干净,就在墙上糊报纸。冬天取暖生炉子,每家外墙都有一个烟筒口。到了春天撤了烟筒,就用报纸塞上那个口。
不知怎地,我家的那个口没塞严,马蜂在里面做了窝,每天成群的马蜂就往楼上的阿姨家飞,搞得她很烦,她就点了把火,想用烟将马蜂熏跑。怎知这把火烧到我家烟筒口上的报纸,顺着又烧到了墙上的报纸。
后来我们经常去小火车站玩才知道,从火车站到我们的驻地是三里地,这个叫程家庄的小站只能停车1分钟。
就是在那个火车站, 我遇到一个农民,当时我正犯鼻炎,他给我吃蜂蜡,特别难吃,但神奇的是,鼻炎居然就好了。
一个留在北京郊外工厂上班的大哥利用探亲假来“八八煤矿”看望父母,带了十斤当时非常宝贵的富强粉挂面,由于当天没有买到兖州到程家庄的火车,楞是沿着火车轨道一路走到了干校驻地。他在干校那几天一直呆在房间里,做了一副扑克牌,我记忆中见过一张黑桃A。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五七干校是非常遥远的故事,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纪念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时,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
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在农村办起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到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下放的干部、家属达10余万人。
当时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在不经意间就会想起。五七干校对于我父母那些长期在机关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一段苦涩的记忆,但在我们当年这些小“五七战士”心里,那确是人生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好时光,广阔的农村大地让我们尽情地撒欢玩耍。
京城翎管王在他的博客里写了一篇《山东邹县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东风五七干校秘闻》。在这篇根据一封篇由邹城市教育局副局长王修东传来的史料,以及京城翎管王重访五七干校的回忆文章里,透过历史的尘埃,极为详细地讲述了我少年时代生活过两年多却不知道一些内幕的细节。
1969年2月,中央直属机关为贯彻落实毛主席《五七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经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批准,来到山东省办“五七干校”。
山东省革委会对中央直属机关在山东办五七干校极为重视,决定将山东农学院白马河农场(东场)全部拨给东风五七干校(此时西场剩余部分全给了6185部队)。
济宁地革委及山东农学院根据省革委的指示确定:1.原白马河农场的职工(包括临时工)由济宁地区革委会负责安排处理;2.原农场的内外债务亦由济宁地革委帮助处理;3.交接双方以实际清点的财务、物资数为移交准数;4.东风五七干校由于建校需要暂时留用四名职工,将来仍由济宁地革委安置。在双方交接报告上,山东农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刁钺代表移交方签字,冯铉(1965年秋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代表五七干校接收方签字。
(邹县五七干校的大门见证了当年五七战士们的生活,神奇的是,它今天还在!)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67军副军长陈新华(1970年下放到山东白马河农场五七干校劳动锻炼4年)为军管领导,配有一个加强排,负责安全保卫。
干校成员分为四个连队,每个连队七八十人(一连:使馆人员,二连:行政机关人员,三连:报务人员,四连:翻译人员)。他们中有二三十岁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六七十岁的老革命、老干部,有的是夫妇二人一起来的,也有带孩子来的。干校人员的工作主要就是劳动生产。
农忙时人员可达四五百人,平时也有二三百人,一部分人居住在兖州兴隆庄煤矿。当时农场宿舍很少,很简陋,很多人挤住在一间宿舍里。1970年,干校盖了八排88间宿舍,后来又盖了四排40多间(现在农场南北两院较为好些的宿舍就是干校盖的)。
另外,干校解决了农场饮水井的问题,打40米深饮水井一眼,建了20多米高的水塔一座(水塔至今仍在使用)。干校把大田分为旱田、水田,1-5条田为旱田,种植小麦大豆,6-8条田为水田,种植水稻。畜牧场主要养猪,另饲养大牲畜30多头,主要是马骡,能同时套7辆马车。
(当年五七战士们住的宿舍。)
京城翎管王文中提到的山东邹县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东风五七干校的旧址就是我爸爸当年劳动的五七干校,我们称为“老点”,他所写的一部分人居住在兖州兴隆庄煤矿(当时叫八八煤矿)就是平时我和妈妈住的地方,被称为“新点”。爸爸周末才会坐大卡车从邹县回来看我们。我和妈妈有时候也会坐大卡车去“老点”。
我对老点的记忆是爸爸工作的厨房和几个人住过的宿舍。像我父亲这样一个出生于县长家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英文专业的大学生,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儿。他还戴着1000多度眼镜,”肩不能扛、手不能拎”,又瘦又小的身子骨无法下大田劳动,领导只好安排他在伙房干活。
由于我父亲在家从不做任何家务活,白案和红案都不会做,领导无可奈何地安排他专门做酱牛肉。来自浙江的爸爸做事很认真和钻研,据说他做的酱牛肉很受欢迎,而我好像一块也没有吃过,因为要凭食堂的菜票才能买。
力红用英语写的一段回忆生动形象,还很有幽默感:It was funny I started to recall some childhood memory. Funny that I have this image in my head, Aunt Zhao smoking in the dark. I was watching the red dot getting brighter and darker with her smoking. I didn't even know women smoked then.
她所描述的这个场景我记忆犹新。当时我俩和几十个干校女战士住在在”老点“白马河农场水库边的一间很大的集体宿舍里,半夜我醒来,发现黑暗中有一个红色的火光一闪一闪,我以为看到了鬼火。
第二天我们这几个女孩聚在一起议论起来,大家都说,是赵阿姨在抽烟。“女的怎么还抽烟呀,女特务才抽烟呢。”在我们那个年代,电影中坏女人的典型道具就是手中有一根香烟。后来这个赵阿姨成了我的婆婆,而且她的习惯是每天都要抽烟。
我和力红豆很怀念在白马河的那段日子。一大清早起床后,我们就拿着牙缸和毛巾到河边刷牙和洗脸。清晨的河水很清,也很凉,这种感觉让我们很兴奋。
我们白天下河游泳。那时候在农村,下河的都是男人,他们脱光了在河里打鱼,看到我们女人也下河,他们一点也不害羞,倒是我们感到难为情了。我就是在那段日子里看到了劁猪和马配种这些在城里和书本里根本就看不到的事情。
在京城翎管王的博文里,还收录了一篇曾经在邹县五七干校”老点“当警卫的回忆,他写得很生动:现在看我们的外交官是多么地风光,西装革履,鲜花迎面,国旗飘扬,国歌雄壮,昂首挺胸地穿行于世界各国,精神饱满地充分体现大国风范。
当年我所见过的外交官却不是这样。他们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朴素的再也不能朴素,平常的再也不能平常。除了他们的面部透着过人的机敏以外,他们的穿着与普通人几乎一样。其中有些驻外使馆参赞级的干部,也经常挽裤腿打赤脚,挑肥担水,穿行于田间。经常是泥一身汗一身,劳动的非常辛苦。后来成为驻日大使的孙平化、肖向前曾经在这里劳动过。
(干校存粮的大仓库。)
这位警卫员回忆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戴眼镜,穿深兰色中山装瘦瘦的人,接近六十岁的年纪,干的最辛苦。好象他把厕所给承包了似的,每天都打扫。他天天挑着粪桶,往返于田间与厕所之间。我多次和他打照面,一张白白的脸,刻有明显的皱纹,我们没有说过话。
有时老兵也和我谈论他们,说别看这些干部现在这副苦相,他们可都是些能人,其中有许多人走过五湖四海,会好几国的语言,见过大世面,能着呢!
当然,这些人里面也可能有敌特,来干校劳动的同时,就是重新审查。你见了他们不要随便说话。老兵这些话,说的我心里沉甸甸的。我所见的实际情况是,所有干部的人身自由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大家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干校经常组织开会、学习、讨论、娱乐,每周都放映电影。
到底是中央机关来的干部,理论水平相当高,我亲眼见过那位掏厕所老同志的讲话,根本不看讲稿,大会发言一讲就是大半天。
(这是当年的五七战士朱宣咸的作品。那时我家晚上点着煤油灯,父亲还是读英文书,从没有放弃学习。)
这篇回忆也让我想起当年那些叔叔阿姨们穿着破旧的衣衫在田里干活的样子,我并不知道这些当时在表面深藏不露的叔叔们曾经和后来是怎样的风光,但是当地的农民形容五七战士的特征是:吃的好穿得破,手上带着大手表。
记得在70年代末,有一次我在看放映电影之前的纪录片时,忽然发现了一个在五七干校穿着大裤衩下地干活的叔叔和中央领导在一起的镜头。妈妈说,他是外交部副部长。
我们在干校经常可以看到露天电影,那是最热闹的时候,周边的老乡也早早就来打谷场占位置了。小红回忆:正片之前总要放一些记录片。那时西哈努克访问中国的记录片一放,当地山东老乡就说:“西瓜努克” 又来啦。西哈努克是我记忆最深的外国领导人。
在京城翎管王这篇博客的留言中,我看到一个叫“彼之耳”的回忆。我猜想一定是认识这个人的,因为我和他的回忆是相同的。他写道:真高兴读到这篇文章,勾起我四十多年前在山东邹县东风五七干校的回忆。当时我还是一名小学生,随父母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多(1970~1972),若非后来要上中学回了北京,恐怕会等到最后与干校一起撤退。
(当年五七战士洗澡的澡堂被拆了。)
我也是在1972年的夏天撤回北京的,原因是那时候爸爸已经“被解放”,提前到北京安顿好了房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1972年2月13日,总参首长作出了“将干校生产移交山东农学院办理”的批示,我们全家又转移到山东济宁的农学院大院中。由于我们住的是学院里,因此住房比在八八煤矿好了许多。
我们住在连排房子里,三间都是朝南的房子,院子里有一个储物间,还有一片菜地,已经锻炼成真正五七战士的妈妈开辟了自留地,种起了蔬菜,还养了鸡。
由于我每天上学走路来回20多里地,又没有公交车,为了让我吃上热饭菜,妈妈用稻草编织了一个大草包,饭菜放在里面一直保持着热度,我天黑回来也能吃上热饭菜。
我们这些在干校的孩子们几乎没有正规地上过学,所有的回忆几乎都是玩耍。玩得最多的是官兵捉贼,我们在农村的田野里大声叫着喊着奔跑着。最初我们没有地方上学,这么多孩子也不能就这样荒了呀。五七干校领导就安排了一些五七战士们来当老师。
这些大学问家们没有经过专门的师资培训,讲课枯燥无味,但有一些老师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小红回忆:干校的学校老师都是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们来当。还记得徐中长吗?他那时年轻,很帅,又会唱歌,大家都喜欢他。徐老师喜欢在宿舍里唱歌,我们就在外面偷听。还有龙老师,一口湖南口音。
力红回忆起一段我爸爸教书的细节:He was teaching us "chun Wen" (Chinese). He was lecturing for a while and started to scream to us "why aren't you taking the note?" We were just 10 years old and could barely write anything.
当时也住8号楼二层的新梅回忆说,黄慧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好像是日文专业的日本归国华侨?长得白白皮肤眯眯眼。她当老师很合适,她那时喜欢和我们一帮孩子玩儿,还没大没小的,去厕所她一个人害怕,像我们中的一员大喊一声“谁去1号”,然后浩浩荡荡带我们进了茅厕,她也不用害怕了。
那个用麦杆搭起的茅房至今让我想起来都有要吐的感觉。一进门处有一口大缸,每天早晨,各家各户将尿盆拿出来,倒在这口大缸中。晚上厕所没有灯光,更是瘆人。只有这个茅厕能让我想念北京家中的马桶,那是多么干净舒服的地方呀。也许正是见识过那么脏的茅厕,现在我出差去偏远的贫困地区再看到茅厕时,也不再感到恶心了。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孩子读书是最重要的事情。妈妈为了让我早一点回北京上初一,在我爸爸回到北京不久,就托一个回京的阿姨把我带了回来,妈妈和弟弟还留在干校。
直到1973年6月20日,中央首长又作出将中直西苑机关五七干校搬回北京的决定。据此,中直西苑机关五七干校1972年3月15日及1973年8月20日按照中直管理处及财政部的文件规定精神,先后分两批向山东农学院进行了有关生产工作、固定资产及物资方面的移交。
1972年下半年,原白马河农场的大部分职工搬回农场,一部分职工则留在了南阳湖农场和接庄果园。1973年8月25日,全体干校人员搬离山东回到机关。至此,中直西苑机关来山东办校,自1969年2月至1973年8月历时四年半。
(干校的小卖部和卫生所排在一起,可以买到肥皂等生活用品,一些小病小灾可以在那里看病。)
我现在回想起在干校的那段时间,正是我父母40多岁,是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工作最出成绩的时候,而他们却把所有的热情和能力都用在修理地球上了。
但在那个年代,对一个孩子来说,五七干校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快乐的日子。正如“彼之耳”回忆的那样:我们几乎不用上课,成天干的是用弹弓打麻雀回家炸着吃,晚上拿手电抓青蛙,水田里钓鳝鱼,带着干校的狗去找王庄、蔡庒的狗打架,手拿玩具枪去劫农村孩子(农村孩子真是可怜,硬是以为我们拿的是真枪)。小红回忆说:还记得我们在大大的麦堆里捉迷藏吗?不玩儿到天黑不回家。
“彼之耳”关于干校伙食的描述就像电影画面一样,一幅幅出现在眼前:干校的伙食好得不得了,算是全国最好了吧,愣让人忘了窝窝头的滋味。吃食堂时,大人伙食费每人每月12元,孩子6元。大米饭白面馒头不限量,(菜定量,每人一份)。后来渐渐地变“修”了,拉家带口的干部便自己做饭(副食自己做,主食去食堂打)。
几乎家家在门前种了黄瓜西红柿等蔬菜,后来发展到家家搭鸡窝垒鸡圈,去集市上买来小鸡雏,养大宰了吃童子鸡。想吃鱼虾了便骑车去南阳湖买,那时鲤鱼草鱼谁吃?只吃鳜鱼呀。记得大虾一斤才四毛,一买一大锅。居家过日子少不了家具和炊具,可缺乏这些东西呀。
说来难以置信,干部们愣兴起了学做家具和煤油炉的热潮。于是不久,家家有了小饭桌小马扎甚至沙发和碗柜。于是各种铁皮糖盒饼干盒,罐头盒成为做煤油炉的绝好原材料,小卖部煤油也成为畅销货。
我想起来,我爸爸居然也令人十分惊奇地做出了煤油炉。小红回忆:那用两个饼干桶做成的小煤油炉子应该是我爸爸的发明创造吧。他不知为大家做过多少个。还记得我爸爸炒的豆芽的味道吗?
当年的食堂已经成这模样了。
小红回忆说,我妈妈那时在“老点”,她那时年轻力壮,在伙房管白案,每天早上3-4点钟就起来发面,和面,蒸馒头窝头花卷糖三角肉包子......最喜欢去“老点”看妈妈,吃妈妈做的蒸馒头窝头花卷糖三角肉包子。)
我们在八八煤矿的伙食也是非常好,我每天负责端着一个锅和一个盛菜的盆去打饭菜。小红回忆:每天去食堂打饭是我最积极干的事。小伙伴们叫到一块儿,成群结队的;还有去打开水,被我打碎的暖水瓶不计其数,都是因为一边走一边玩儿,一不小心就摔碎了暖水瓶,回家一定少不了一顿骂。
食堂有两个盛菜的人很不招人喜欢,大家给他俩起外号,一个叫哆嗦,一个叫半勺。我妈妈有一段时间负责食堂的白案,我经常去找她,就学会了做花卷。
干校的粮食和蔬菜都是五七战士们自己种的,都是当年的新粮食和新鲜蔬菜,但是饲养的猪不够吃,猪肉还是需要进城采购。每当我看到干校的桑连长开着拖拉机出门时,我就知道,他去兖州城里的肉联厂去买排骨,那些排骨上挂着特别多的肉,吃起来非常香。
30年后,我在国外见到桑叔叔,这个操着一口地道山东话的大叔一边开着白色奔驰,一边给我讲述他当年在干校开着拖拉机去采购猪肉的往事。
力红回忆说:the leader of local farmers (duai chang) was telling the Villagers that "when the communism (gong chan zhu yi) is realized, we will be eating as well as the people in "Gan Xiao". 拼音是共产主义和干校。
虽然我去五七干校时才10岁,但是跟着妈妈学着种蔬菜和地瓜,每到三夏和三秋时节,我们也下地收拾庄稼。农村的广阔天地练就了我们这些城里孩子有一副强健体魄和热爱劳动并珍惜粮食的品质。
“彼之耳”的这段描述就像是我自己说的一样:“回北京上中学后,学校组织学农劳动,农村同学还纳闷呢,这帮西苑机关的孩子割麦子,打要子,拔秧、插秧熟练程度一点不亚于他们,却不知道我们曾有过五七干校的经历呢。”
(2009年,David 刘重回五七干校,找到了当年的李兽医。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从来没有回过山东五七干校的原址,那个叫八八煤矿的地方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兴隆庄煤矿。据一个朋友说,前几年他们去当年八八煤矿旁边的村庄寻找当年的农村玩伴,居然还有一个人记得新梅,因为她有一个农村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姓:司徒。
一时激起千层浪,一篇五七干校的记忆,引发了我大学同学LL回忆起当年他们和父母下干校时的许多故事,现在谈起来很有趣:
我正在法国东南部一个世外桃源休假。看到这篇文章也触动了我的五七情结。我去的是样板团五七干校,计有中央乐团,中国芭蕾舞剧团一部分,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一团,北京京剧二团。地点是风景如画的昌平小汤山。在小汤山中学读了三年。
对我这个城里象牙塔出来的孩子一下子融入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当中,夏天去温榆河,大运河摸螺蛳游泳,冬天滑冰。一年四季的农活都干过,插秧,割麦,拾粪,在试验田种杂交高粱,到果园摘梨摘桃摘苹果。
食堂的菜肴可口,每三个星期班车回京一次。还可以去小汤山温泉浴池洗浴。最难以忘怀的还是有琴房可以练钢琴,小提琴及各种乐器。乐团,芭团乐队刚从音乐学院分来没几年的年轻修正主义音乐尖子和我们几个孩子玩在一起。晚上用棉被毯子把门窗堵上,听他们演奏老柴,莫扎特,巴赫,勃拉姆斯,海顿......一起畅谈世界古典文学,古典音乐。始知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是无论如何压抑不住的!这段时光永远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住在我旁边铺位如今在国外的潘女士讲了她父母在干校时的有趣事情:
文章的确勾起我对干校的回忆。我们去的是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名家文人成群:冰心,沈从文,张光年,范增,臧克家,郭晓川......可最让当地老乡奇怪的是这群文化人里既有做鞋(作协)的还有取鞋(曲协)的。当听说我们的鸭官一月工资300多,老乡问“那鸭蛋要卖几多钱一个。
这是我们那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一位在新西兰的发小留言说,你所写的五七干校的经历也正是我的经历,我们应该认识,你是女生,我是男生,应该没有在一起玩过。东风五七小学毕业后,我们去当地的一个叫兖州道沟中学上学了。神奇的是,由这封留言,我找到了这位小名叫四毛的发小,而且他曾经就和我住在一个单元里。
我在福建的表哥说,想起40多年前,正是你们去干校,我们收到一封邮局发来的提货单,要求3天内将山东兖州来的货物提走。
家里人都纳闷,山东没有什么有联系的人啊?第二天收到来自山东兖州某五七干校信,就是你文中写的会抽烟赵阿姨我的姑妈写给我爸的,说是她去了干校,当地盛产苹果,又是收获季节,很便宜,于是就通过货运给福州寄了一筐。
那时流通不畅,产自北方的苹果在南方很金贵的,去提货的任务自然“光荣”的落在我身上,当时我刚上中学也就13-14岁,骑着自行车到福州东郊火车货站提货时愣住了,少说也有60-70斤的苹果,装在用藤条编织大筐内,比我想像的大得多,我怎么弄回家?
好在货场搬运师傅问我你会带人吗?我说会啊,他说,人比它重你都能带怕什么,我帮你把它捆在后架上,扶你上车你就一直骑回家。好在那时路上机动车少,也没几个红绿灯,近一个小时的路程,一口气到家。第一次完成“重大任务”印象深刻!
此后几年,每当收获苹果的季节,我们都收到来自山东兖州的货单,直到姑妈回京。姑妈在干校身处逆境还不时关心大家,让我们感动至今!
人生的每一段记忆,都是珍贵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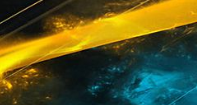




评论列表